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完美,堪称代表我国古代小说巅峰的文学名著,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是引人入迷,百读不厌的经典之作,是足以世代相传、流芳百世的文化瑰宝。然而也有不少当代的读者感到《红楼梦》读不通、读不懂、读不下去。[1]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跟曹雪芹生前未能给我们传下他创作的完整的《红楼梦》,现在我们读到的《红楼梦》,都是经过后人校补,存在着种种不完善甚至不通之处,大有关系。现在流传的《红楼梦》大致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在曹雪芹逝世30年后,经程伟元、高鹗在搜集流传的抄本的基础上辑补、刻印的《红楼梦》(简称程本),如1982年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以及现在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皆属程本;另一种是直接根据脂砚斋评本前80回(简称脂本),再补上程本的后40回,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由红学所以庚辰脂本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这两种版本,既各有优点,又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笔者长期研究《红楼梦》的语言艺术[2],深感有必要打破脂本与程本的界限,根据“择善而从”的校勘原则,重新校注一部弃各本之短而集各本之长的《红楼梦》,使之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更好读好懂,以具有会校、精注、现代版的特色,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本书的校勘,由于是以庚辰脂本为底本,因此它就避免和纠正了经过程伟元、高鹗修改的程本《红楼梦》的众多谬误:
避免和纠正了程伟元、高鹗为使该书“不谬于名教”[3],而对曹雪芹原著中直接反对封建名教之处所作的蓄意篡改。如第2回脂本写道:“成则王侯败则贼”。程本把其中的“王侯”改成“公侯”。“王”是指最高统治者,改成“公”,显然就把批判的矛头从最高统治者的身上避开了。又如第15回写北静王把“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一串”转赠给贾宝玉,程本把脂评本中的“亲赐”改成“所赐”。“圣上亲赐”是指皇帝亲手赐予,这跟次回作者写林黛玉骂它是“什么臭男人?过的”,“遂掷而不取”,前后相呼应,说明黛玉或许不知道它是皇帝?过的,而作者既然写明它为“圣上亲赐”,就显然有借此骂皇帝也属“臭男人”之意。程本改“亲赐”为“所赐”,则显是蓄意避免把皇帝也骂为“臭男人”。又如第16回脂本写皇帝之所以同意贾元妃省亲,乃因“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女儿,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程本将其中带“·”着重号的字句删去,岂不显然是为了掩盖由于皇帝的“禁锢”而造成“甚至死亡”的惨剧么?在第18回中曹雪芹分明说他绝不屑于写“省亲颂”脂本的回目为“荣国府归省亲元宵”,程本为了突出歌颂“皇恩”,而将回目改成“皇恩重元妃省父母”,这不是公然跟曹雪芹所表明的创作意图唱反调么?
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第2回脂本写“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把在封建社会被视为最卑下的女儿,说成比大乘佛教尊崇的佛和道教尊崇的神“还更尊荣”。其反封建的精神,令人实在可钦可佩至极!然而程本却把这改成“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这一改不只改掉了对女儿地位的极高尊崇,而且把女儿视为如同瑞兽珍禽、奇花异草一样,是供统治阶级的玩赏之物了。第34回脂本写袭人对王夫人说:“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的连畜牲不如。”这无异于说,菩萨和畜牲本是一回事,只因人“心顺”与“心不顺”的说法不同罢了。程乙本则把后一句改成“就没有忌讳了”。这不仅失去了语言本身的形象性,还清楚地暴露了篡改者思想上的忌讳,生怕对封建传统思想有所冒犯和亵渎。
避免和纠正了程伟元、高鹗为使该书符合自己的庸俗趣味,而对书中某些蕴藉含蓄、寓意深邃的笔墨所作的浅露平庸的修改。如庚辰本第12回脂批所指出的:“《石头记》中多作心传神会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便入庸俗之套。”而程本的修改,则往往有此弊病。如第19回茗烟向宝玉介绍跟他私通的一个女孩子。因“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卍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脂本接着写:“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说着,沉思一会儿。”究竟宝玉认为他将来有什么“造化”,“沉思”的又是什么,脂本皆含蓄不露。这就引人遐想,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和耐人寻味的余地。而程乙本却改成“宝玉听了笑道:‘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作媳妇好不好?’茗烟也笑了。”这就把“造化”和“沉思”的内容坐实为“说给你作媳妇”。不仅显得很庸俗,而且跟宝玉平日最厌恶女孩儿出嫁的思想性格相悖。就在该回袭人说到她的表妹要出嫁,还写到“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两声,正不自在。”他怎么会一变而自己要当媒人,叫女孩儿出嫁呢?
脂本的语言往往能由表及里、由小见大地开掘其内涵深邃的社会典型意义。如第6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脂本写宝玉“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它由此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毒辣,使袭人被主子糟蹋了,还以“亦不为越礼”而自慰。程甲本把其中的“强”字改成“与”字。这即改变了袭人不得不勉强屈从的阶级地位和可悲处境。程乙本改“强”为“强拉”,又把“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这句直接控诉封建礼教对袭人毒害之深的语言,改成“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遂只得和宝玉温存一番。”以“温存”代替“偷试”,又删去“云雨”二字。这一改,仿佛袭人未和宝玉发生性关系,由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毒害,变成少男少女之间调情的恶作剧,显得庸俗透顶而毫无深意可言。
第75回写邢大舅与薛蟠等人赌钱,两个娈童只趋奉赢家不理输家的,脂本接着写邢大舅“因骂道: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洑上水。”而程本却把形象地揭露趋炎附势这一丑恶社会现象的“专洑上水”四字,改成纯属骂人的“真是些没良心的忘八羔子!”脂本接着写邢大舅乃拍案对贾珍叹道:“怨不的他们视钱如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钱势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老贤甥,昨日我和你那边的令伯母赌气,你可知道否?”贾珍道:“不曾听见。”那大舅叹道:“就为钱这件混账东西。利害,利害!”这种由小见大——由两个小娈童的势利,而旁及到“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为“钱势”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的描写,仿佛如晴天霹雳一样,给人以石破天惊的巨大震撼。而程本却把上述带着重“·”号的字句全部删掉,剩下的只是邢大舅与邢夫人之间赌气,成为小事一桩,何足挂齿?
避免和纠正了程伟元、高鹗为体现自己的爱憎感情,而使人物形象被删改得变形、失真之处。如贾宝玉性格的重要特征是对女孩儿的亲近和同情。他因看到金钏儿为午睡的王夫人捶腿很疲倦,“就有些恋恋不舍的”,便掏了一丸香雪润津丹给她,并说要向太太讨她到怡红院去。不料“王夫人翻起身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还要把她辇出贾府,以致迫使金钏儿投井自杀。脂本写的是“金钏儿含羞赌气自尽”,宝玉则“此时一心总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而程乙本却删掉了其中的“赌气”二字和“跟了金钏儿去”一句。后来宝玉带着小厮茗烟到水仙庵焚香祭祀金钏儿,脂本写茗烟代祝:
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
程本却把上述茗烟代祝的话改成:
你若有灵有圣,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你也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玩耍,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第43回)
经过程本的删改,不仅使金钏儿的自尽改成纯属个人的责任,而且阉割了宝玉视金钏儿为“知己之间”的平等思想,把“来生也变个女孩儿”,以表示对身为封建社会的“须眉浊物”的憎恶和愤绝之情,篡改成仅是为了和女孩儿好“一处玩耍”,“两下里都有趣”,这就大大扭曲了宝玉对金钏儿的高尚、纯正感情,削弱了宝玉性格的叛逆性。
宝玉性格的叛逆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劝他走封建人生道路的深恶痛绝上,他斥之为说“混账话”。宝钗因为说混账话,他就和她“生分了”;黛玉由于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他就认定她为“知己”,倾心相爱和深敬。可见说不说混账话,这对于宝玉形象该是多么至关重要!而程本竟将脂本中的“混话”一词,也统统改成“混账话”。混话,即混说,并无骂人的意思。如《儒林外史》第5回有“只管讲这些混话,误了我们吃酒”。而“混账话”,则是骂人无理无耻,岂能与“混话”相混淆?宝玉与黛玉在共读《西厢》时,以《西厢》中的词句对黛玉进行爱情试探,引起黛玉“不觉带腮连耳通红”,指责宝玉是“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程本即将其中的“混话”改成“混账话”,变成宝玉本人也说“混账话”,遭到他的知己黛玉的斥责。第39回脂本写宝玉听信刘姥姥说的某个庙里有茗玉小姐的像,叫茗烟去寻找,茗烟未找到,说:“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碰头。”程本也把这里的“混话”改为“混账话”。这些本来都是为了突出宝玉多情的性格,而程本修改者却斥之为“混账话”,使宝玉变成不但自己好说混账话,还听信别人说混账话。
“金玉姻缘”邪说,是宝玉最受困扰的精神枷锁。脂本写宝玉有一次“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第29回)程本却把这表示愤绝的“抓下”改成平静的“摘下”,把“我砸了你完事”这愤极恨绝、斩钉截铁的语言,改成轻松平淡地说:“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这一改,使宝玉那急欲砸烂“金玉姻缘”枷锁的痛苦神情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力量,也即随之糟蹋殆尽。
不但宝玉等主要人物形象横遭扭曲,许多次要人物形象也被改得变味了。如袭人为顾全宝玉的“声名品行”,向王夫人进言,要叫宝玉搬出大观园去住。这时脂本写王夫人道:“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你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第34回)它说明王夫人之所以要保全宝玉的“声名体面”,是因为“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这不仅揭示了“妻因子贵”的封建家庭关系实质,而且突出了王夫人那利己主义的性格特色。可是程本却把“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改成“难为你这样细心”;把“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改成“别叫他糟蹋了身子才好”。仿佛王夫人真的完全是从关怀、爱护宝玉出发,而不是为了保全她自己的地位和声名体面。这岂不把王夫人与宝玉之间本属封建卫道者与叛逆者的关系,扭曲成一般的母子关系了?
马克思曾经赞扬巴尔扎克“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4]。曹雪芹对人物形象描写的最大成功,我觉得也就在于他对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程本的修改,在许多地方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甚至使人物性格被改得失真、变形,也就在于修改者对原著所描写的人物性格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而深刻的理解。这是我们之所以认定脂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而要纠正程本误改、妄改的根本原因。
避免和纠正了程伟元、高鹗将曹雪芹原著中用词形象生动、准确传神,改得抽象呆板,模糊失神,甚至字句不通之处。用词是形象化,还是抽象化,是艺术语言与非艺术语言的重要区别之一。看来程本修改者并不十分懂得这一点。他往往使用词由形象化改为抽象化,如脂本写贾母等听到元春被封为贵妃的消息,“都洋洋喜气盈腮”,程本改为“皆喜见如面”(第16回);脂本写宝玉听到贾政叫,“好似打了个焦雷”,程本改成“呆了半晌”(第23回);脂本写倪二“抡拳就要打”,程本改成“就要动手”(第24回);脂本写贾母听张道士说宝玉的形容身段、言谈举止,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便“由不得满脸泪痕”,程本改成“由不得有些戚惨”(第29回);脂本写黛玉以为宝钗在她母亲跟前撒娇,是“故意来刺我的眼”,程本改成“故意来形容我”(第57回);脂本写凤姐说:“少不得我去拆开这鱼头,大家才好”,程本改成“少不得咱们按着这个法儿才好”(第68回);脂本写“诸务猬集”,程本改作“诸务烦杂”(第70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程本不仅往往使用词失去形象性,更重要的还由此而使人物形象受到损害。如脂本写李嬷嬷说林黛玉“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8回)。这个“尖”字,既是“刀子”的形象化,又突出了林黛玉那说话犀利、尖刻,对封建世俗之见,勇猛无情地直刺过去的叛逆性格。可是经程本把这个“尖”字改成“利害”,就失去了用词的形象性和准确性,使林黛玉的性格仿佛如泼妇一样利害。又如脂本写凤姐协理宁国府,“喝命”处罚迟到的佣人时,众人“又见凤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第14回)。庚辰本脂批说,这“眉立二字如神”。它把凤姐那凶狠气恼的神情和凶神恶煞般的形象,皆刻画得可谓生动传神至极。可是经程本改“眉立”为“动怒”,就抹煞了凤姐动怒的个性特色,使凤姐形象的生动性和可憎性也为之削弱。
从程本的许多修改来看,修改者与原作者曹雪芹的语言艺术修养和创作才能,确实差距甚大。曹雪芹能活用汉语,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语言艺术大师。如脂本写“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这个“猴”字本是名词,这里用作动词,便使宝玉那猴子般机灵、撒娇的形象活现。庚辰本于此处的夹批指出:“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程甲本把这个“猴”字改成“挨”,变成“便挨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第14回)。不仅失去了宝玉形象的生动性,而且改得字句不通了。“挨”,是靠近的意思,只能挨向凤姐身边,又怎能“挨向凤姐身上”呢?它跟凤姐接着说的“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也衔接不上。又如在宝玉住进大观园前,贾政叫他前去叮嘱几句,脂本写宝玉先是“杀死不敢去”;不得不去,又“一步挪不了三寸”;到了门口,“只得挨进门去”;听完叮嘱,便“一溜烟去了”。这把宝玉由畏惧、紧张到胆怯、小心,再到如释重负,欢快地溜回的心理、神态,皆刻画得层次分明,清晰可见。程本未改前后文,独把当中的“只得挨进门去”,改成“只得挨门进去”(第23回)。“挨进门去”的“挨”,应读ai(捱),是艰难地忍受、拖延的意思,如“挨打”、“挨时间”,写他进门时的小心谨慎、痛苦不堪和缓慢而进的样子。而一经程本改成“挨门进去”,这个“挨”便应读ai(埃),是顺着、靠近的意思。他不挨门进去,难道还能破门而入?这完全成了废话,失去了原来表现宝玉不同的心理层次的作用。
如果说个别字句的不当,也许是由于抄写或印刷过程中的误抄或差错,在脂本中也不难找到字句不通的许多例证;那么,大段文字修改得笨拙,程本修改者就更难辞其咎了。如脂本写秦钟与智能私通——
正在得趣,只见一人进来,将他二人按住,也不则声。二人不知是谁,唬的不敢动一动。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听声方知是宝玉。
程本把这一段改成:
这里刚才入港,说时迟,那时快,猛然间一个人从身后冒冒失失的按住,也不出声,二人唬的魂飞魄散。只听“嗤”的一笑,这才知是宝玉。(第15回)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原著是源于生活的写实。它把秦钟与智能二人“正在得趣”之时,突然被人按住而“唬的不敢动一动”的紧张情景,把宝玉那“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的逗人的神气,皆写得新鲜别致,生动如画,使读者有身历其境的真实感。而程本改成“这里刚才入港,说时迟,那时快”,“唬的魂飞魄散”,则纯属说书人的陈词滥调,它可以四处套用,缺乏特定情景的新鲜感和生动活泼的独创性。是追求写实的新鲜独创,还是因袭传统的俗套,看来这正反映了曹雪芹的原著与程本的修改者在语言艺术上的不同特色,而笔者此校注本就是要力求恢复和保持曹雪芹原著的语言特色。
二、本书的校勘虽然以庚辰脂本为底本,避免和纠正了程本的诸多谬误,但是笔者认为,程本的功绩还是主要的,何况程本的底本也是根据程伟元、高鹗当时所搜集到的传抄本,庚辰本等所有的脂本,虽然更接近曹雪芹的原著,但它们并不是曹雪芹的手稿本,而是经过多人辗转传抄的传抄本,其中抄错、抄漏、臆改、误改、妄改之处很多,可谓错误百出。脂本与程本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如俞平伯所说:“互有长短。”[5]因此,不只庚辰本前80回缺第64、67回,本书据程甲本补,后40回以萃文书局程甲本为底本,而且全书依据“择善而从”的校勘原则,也吸取程本的长处,校正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通行校注本中诸多谬误不通之处:
由语句不通,校正为语句通顺、畅达。如庚辰本及以庚辰本为底本的通行本第1回写道:“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如果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生活,“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那当然是对的,而“晨夕风露,阶柳庭花”,是极富诗情画意的自然美景,理应更觉润人笔墨,怎么会把它也说成是“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呢?这叫读者怎么能读的通呢?曹雪芹怎么会写出如此不通的语句呢?笔者依据程甲本,把此句校正为:“故当此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夕风露,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这就不仅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而且以“晨夕风露”来“润人笔墨”,显得极富想象力,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又如庚辰本及以庚辰本为底本的通行本第8回写薛宝钗的性格特征:“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可是事实上宝钗其人乖巧极了,她一点儿也不“愚”,哪用“藏愚”呢?说她的“罕言寡语”是“藏愚”,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为了解决这个语句不通,甲辰本把“藏愚”二字改成“藏语”。可是这样一改,又跟前句“罕言寡语”,成为毫无必要的语义重复。通行本于此处加注曰:“藏愚:藏智巧于愚讷的外表之中。”既然是“藏智巧”,那怎么又叫“藏愚”呢?如此曲里拐弯、深文周纳的释义,岂能令人信服?笔者依据程甲本,将此句校正为:“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只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而且以“人谓装愚”,一语揭穿了宝钗“罕言寡语”的实质,既由表及里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又说明群众的眼睛雪亮。
由语意不明,校正为语意清晰、明白。如庚辰本及以庚辰本为底本的通行本第4回写冯渊遇见英莲,“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后方过门”。这段话令人不解的是:他“立意买来作妾”,“不再娶第二个”也罢了,为什么中间又插上了一句“立誓再也不交结男子”呢?难道他要与世隔绝,与天下所有男子绝交?即便如此,这跟他娶不娶“妾”又有什么相干呢?再说他既然如此喜欢这丫头,为什么还要“三日后方过门”,而不立即或“三日后”即过门呢?笔者查对甲辰本、程甲本,才恍然大悟。原来甲辰本、程甲本此处的“男子”,是写作“男色”,买了这个妾之后,他“立誓再不交结男色,也不再娶第二个了”,这就顺理成章,语意清晰了。至于“所以三日后方过门”,据甲辰本、程甲本,应作“所以郑重其事,必得三日后方过门”。原来是庚辰本、通行本脱漏了其中“郑重其事,必得”六个字,才人为地造成了语意不明,使读者百思而不得其解。
又如第39回,庚辰本及以庚辰本为底本的通行本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带来了一些瓜果菜蔬,凤姐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那些沉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儿再去。”周瑞家的说:“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这也罢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请了来我见一见。’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缘分了。”何谓“天上缘分”?难道是天上牛郎织女般的缘分?跟这儿的上下文完全扯不上呀!笔者据程甲本,把这句校改为:“这可不是想不到投上缘了。”由“天上缘”改成“投上缘”,这不仅使语意由晦涩变为清晰,而且与周瑞家的开头所说“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显得前呼后应,文意贯通。何况己卯本在“天”字旁用朱笔写了个“投”字,庚辰本旁改“天”字为“投”字,皆证明这个“天”字是误抄,程甲本用“投”字当属曹雪芹原稿如此。而红学所校注的人文版通行本,1982年版及1995年修订版皆用“天上缘”,直到2008年第三版才采纳鄙人之见改为“投上缘”。[6]
由用词不当,校正为用词准确、生动。如第25回庚辰本及人文版通行本皆写宝玉“若要点名唤他(指红玉)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寒心;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若好还罢了,若不好起来,那时倒不好退送的”。这里宝玉所担心的应是“怕袭人等多心”,即多生怀疑之心,而不是“寒心”——因失望而痛心。宝玉所不知的是红玉属“何等性情”,不可能也不必要细究她的具体“行为”属“何等”。因此笔者据甲辰本、程甲本,将“寒心”校改为“多心”,将“行为”校改为“性情”。
又如第2回庚辰本及人文本写贾雨村要娶姣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姣杏送进去了”。“屁滚尿流”,历来没有用于形容人“喜的”,只用于形容人惊慌恐惧得狼狈不堪的形状。如《水浒》第75回:“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元曲选》康进之《李逵负荆》第4折:“你要问俺名姓,若说出来,真唬的你尿流屁滚。”“喜的”与“吓得”、“唬的”情景相差甚巨,岂能混用?难道封肃不是“喜的”而是“唬的”?若是已经“唬的屁滚尿流”,那么又何必“巴不得去奉承”呢?若说封肃果真“喜的屁滚尿流”,那就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神经或生理有毛病?可见这“屁滚尿流”一词用在这里无论如何说都不恰当。一看甲辰本、程甲本就明白了,原来这里是作“封肃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据脂批,封肃其名是喻“风俗”。一听说本府有个当大官的贾雨村要娶自己的女儿姣杏作二房,就“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这不恰恰是世风日下的反映么?不是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封肃那势利小人的市侩性格么?程甲本这“眉开眼笑”一词既有甲辰本为根据,又与上下文所写的人物性格相契合,人们有何充足的证据断言它不是出自曹雪芹原稿呢?退一步说,即使这属于后人的改笔,只要它确实改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纳而偏要弃优取劣呢?《红楼梦》中所引用的《西厢记》曲文,如第49回贾宝玉赞赏的“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就是属于金圣叹的改笔,而据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文,则是“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
由重复累赘,校正为简洁明快。如第24回庚辰本、人文本写:“次日一过五鼓,贾芸先找了倪二,将前银按数还他。那倪二见贾芸有了银子,他便按数收回,不在话下。这里贾芸又?了五十两,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这段仅两行的文字,即两次出现“不在话下”,又是“按数还他”,又是“按数收回”,难道还银子还有不“按数还”、不“按数收”的么?曹雪芹的文笔怎么会如此重复累赘、废话连篇呢?笔者据程甲本将此段文字校正为:“次日五更,贾芸先找了倪二,还了银子,又?了五十两银子,出西门找到花匠方椿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这就由庚辰本的69个字删成41个字,精简近四分之一,使文笔显得简洁明快多了。值得注意的是,梦稿、甲辰本也无“一过”二字,梦稿、郑藏、列藏、甲辰本“五鼓”也皆作“五更”,梦稿、郑藏本也没有两句“不在话下”,甲辰本则跟程甲本同样删掉了“将前银按数”,“他那倪二见贾芸有”、“他便按数收回”等多余的话,可见这段文字各本本来就有异文,程甲本绝非没有版本根据的妄删。何况他删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择善而从”?
由上下文衔接不上,自相矛盾,校正为上下文衔接紧密,合情合理。如第15回庚辰本、人文本写馒头庵的净虚老尼为张金哥的婚姻官司托凤姐给长安节度云老爷说情,“凤姐听了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稀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叫他?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这里凤姐开头说的“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显属故意推托之词,老奸巨猾的净虚怎么会听不出来,竟然会“听了,打去妄想”?既已“打去妄想”,接着怎么会又用激将法的语言,使凤姐终于“便发了兴头”?可见这“打去妄想”四字,是与上下文矛盾,不合情理的。程甲本这四个字作“攒眉凝神”,说明老尼净虚一听就听出凤姐是推托之词,经过“攒眉凝神,半晌”想出了用激将法的语言,这才使凤姐由借故推脱变为“发了兴头”。凤姐态度的转变,使净虚终于如愿以偿。老尼的“喜不自禁”,不只是由于她的目的达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攒眉凝神”,表明其多谋善断、老奸巨猾的性格,足以使表面上说“我也不等银子使”而内心里却极为贪婪钱财的凤姐成为她的手下败将,甘心为她所利用。因此,这“攒眉凝神”四字,无论对于净虚或凤姐的性格刻画得既老谋深算,又活灵活现,都可谓是不可替代的神来之笔!由粗疏简略,增补为曲折复杂、细腻动人。如第74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在写了晴雯怒气冲冲地将箱中“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之后,庚辰本及其他脂本皆未写王善保家的与晴雯有进一步的交锋,显得过于粗疏简略,使人物性格未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本书则根据程甲本、程乙本增补了——
(王善保家的)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察;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她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
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脸,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刚要还言,凤姐道:“妈妈,你也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你且细细搜你的;咱们还到各处走走呢,再迟了,走了风,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这口气。
笔者早就指出:“增加这段描写,既展开了被压迫者与狗腿子、狗腿子与主子之间的性格冲突,又揭示了在王善保家的与凤姐背后邢夫人与王夫人的矛盾。它说明晴雯的反抗之所以暂时得逞,绝不意味着封建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宽容,而只是由于她敏锐地看准和机智地利用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王善保家的之所以‘且忍了这口气’,也绝非慑于晴雯的厉害。而是由于‘凤姐奸甚’(商务版《增评补图<石头记>》对凤姐‘忙喝住晴雯’的夹批),使身为宠犬的她无可奈何。并且进而使晴雯的愤怒和反抗,机智和尖刻;王善保家的骄宠与凶狠,刁钻与脆弱;凤姐的奸诈与阴险,伪善与圆滑;各人的复杂性格皆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示。给读者留下了精彩纷呈、忍俊不禁的绝妙印象。”[7]
可是这段极其曲折复杂、细腻动人的文字却成了脂本和人文版通行本的脱文。为什么红学所校注的人文版《红楼梦》对此段脱文不予校补呢?仅因为它出自程本么?众所周知,程本也是以曹雪芹手稿的传抄本为主要依据的,程伟元、高鹗当时所见到的传抄本比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要多得多,人们绝无充足的证据断定这段文字不是出自曹雪芹的手稿。退一步说即使它出自后人的补笔,只要它确实补得好极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加以排斥呢?经过毛宗冈父子修改的《三国演义》,不是比嘉靖本罗贯中不分回只分240则的《三国演义》更受读者的欢迎么?因此本书对程本也不抱偏见,只要它补得确实好,就同样依据“择善而从”予以校补。
三、本书虽以庚辰本为底本,但对庚辰本中的许多谬误,也依据其他脂本作了“择善而从”的校正。
校正因同音或音近而误的文字。如庚辰本第36回写宝玉说:“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胡谈乱劝”岂能“邀忠烈之名”,又怎么还会“即时拚死”?原作者不可能写得如此前后矛盾。文官对朝廷的错误有弹劾、进谏之责,甚至为此而不惜“拚死”,以“邀忠烈之名”。因此这“胡谈乱劝”,显然是“胡弹乱谏”之误,是抄胥因两者音近而造成的笔误。这不仅是一种推测,而且有舒序、甲辰、程甲本作版本根据,它们此处皆作“胡弹乱谏”。作者写宝玉如此斥责“胡弹乱谏”,其矛头所指就不只是文官,而且还直指封建的弹劾、进谏制度的虚伪、骗人。可惜有的通行本(包括2008年以后的人文本,下同)却把庚辰本抄胥的误抄强加在曹雪芹头上,而对“胡谈乱劝”不予校正。
校正因形似而误的文字。如庚辰本第51回写李纨说:“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小”到初生婴儿,难道也能“人人皆知皆说”么?这显然说不通!通常也只说“老少男女”,没有“老小男女”一说。此处除庚辰本外,各本也皆作“老少男女”,庚辰本显然是因“小”与“少”形似而误抄。如此明显不通的错字,有的通行本竟也以错传错,可见其对庚辰本的迷信已到了近乎盲从的地步!
校正其他明显错误的文字。如庚辰本第三回回目“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且不说以贾雨村与林黛玉相提并论,显得多么不伦不类,有损林黛玉的形象;称“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更不恰当,文内作者分明写林黛玉“原不忍弃父而往”,“无奈他外祖母致意务去”,其父又说:“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林黛玉“方洒泪拜别”乃父,回目上怎么反而说是她“抛父”呢?原作者不可能自己使回目与本文相矛盾。甲戌本此回回目作“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在“收养”二字旁还有脂评曰:“二字触目凄凉之至。”作者也确实是以极其同情的笔调来写林黛玉的。舒序本作“讬内兄如海酬闺师,接外孙贾母怜孤女。”程甲本作“讬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其他如蒙府、戚序、戚宁、甲辰、列藏本皆同作“讬内兄如海酬训教,接外孙贾母惜孤女”,都体现了对黛玉的同情。本书採用的就是蒙府等五个脂本的回目,而与人文本责备“林黛玉抛父进京都”的回目迥然有别。
校补脱漏的字句。如因漏“迟”字而使语意不通。黛玉到贾府后去拜见各位长辈,邢夫人要留黛玉吃晚饭,“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这里“不恭”的不是“领了赐去”,而是因“领了赐”而迟去。故这里漏了一个“迟”字,据甲辰、程甲本,本书校补为“恐领了赐迟去不恭”。此系庚辰本抄胥因“赐”“迟”同音而漏抄一个字,而通行本却未予校补。
校补两句以上的脱文。如第25回写赵姨娘悄悄说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来,真真把人气杀,叫人一言难尽。我白和你打个赌,明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她搬送到娘家去了,我也不是个人。”()内为脱文,当系庚辰本抄胥因“主儿”、“明儿”两个“儿”字相同而漏抄一行22个字。本书据列藏、梦稿本补。2007年前的人文版等通行本未予校补,就使“了不得!了不得”的惊叹,与“提起这个主儿……”衔接不上,缺“明儿”二字,“这一分家私……”跟末句打赌的口吻“我也不是个人”,更不相契合。因此列藏、梦稿本多出的这段文字,定为曹雪芹原稿所有,绝非他人所能妄补。
删除妄增的衍字衍文。如第25回写贾环“要用热油烫瞎他(指宝玉)的眼睛。因而故意装作失手,把那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一推”。这里写烫的是脸,而接着写的却是“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后面写的又是“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出来”,黛玉来瞧时,宝玉“忙把脸遮着”。可见被烫的只是脸,“头”上并未烫着,所谓“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其中的“满头都”三个字属衍文,不删则与上下文皆相矛盾。原作者曹雪芹不可能在相距仅几行字之间就写成前后自相矛盾的话。它显然是属于庚辰本抄胥的误抄;甲辰、程甲本此处就没有这三个衍字,显得上下文契合无间。我们虽尊重庚辰本,但绝不迷信它,直至第三版人文本才据敝见,依照甲辰、程甲本删去其“满头都”三字。纠正人文本的误改。如第39回写贾府吃螃蟹,人文本写作“一斤只好秤两个三个。这么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平儿道:‘那里够,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并作“校记”曰:“‘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原作‘也没有摸着吃的,也少’,从各本改(“得”或作“的”)。”其实,这不需校改,只要把“平儿道”后面人文本的标点改一下,作“哪里够!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的也没有,摸着吃的也少。”这就通顺了。人文本校改后,反而不通:何谓“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螃蟹放在那儿,怎么会有是否摸得着之别呢?
以上只是举出个别的例证;类似的校改,在全书达二千处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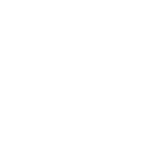
 2023年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
2023年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 安徽网库讯:兵团战友进江汽厂50周年纪
安徽网库讯:兵团战友进江汽厂50周年纪 安徽网库讯:庐江县郭河镇举行“金秋助
安徽网库讯:庐江县郭河镇举行“金秋助 安徽网库讯:线上发布安徽省企业社会责
安徽网库讯:线上发布安徽省企业社会责 安徽网库讯:热烈庆祝2020年全省工业行
安徽网库讯:热烈庆祝2020年全省工业行 安徽网库讯:衡山镇召开凤凰城建材市场
安徽网库讯:衡山镇召开凤凰城建材市场 安徽网库讯:“千村百镇唱大戏”走进金
安徽网库讯:“千村百镇唱大戏”走进金 安徽网库讯:庐江:满地“黄金甲”脱贫
安徽网库讯:庐江:满地“黄金甲”脱贫 安徽网库讯:长三角地区首届中国工业大
安徽网库讯:长三角地区首届中国工业大
 青岛一“钉子户”房屋四周被挖空成“孤
青岛一“钉子户”房屋四周被挖空成“孤 高清:湖南男子带3岁儿子冬泳 河水冰冷
高清:湖南男子带3岁儿子冬泳 河水冰冷 中国富商携儿子乘飞机视察法国葡萄园时
中国富商携儿子乘飞机视察法国葡萄园时 澳洲洋女婿迎娶西安姑娘 女方娃堵门要红
澳洲洋女婿迎娶西安姑娘 女方娃堵门要红 “私人定制”风靡深圳富人圈
“私人定制”风靡深圳富人圈 组图:济南放生两千斤鲤鱼遭“疯狂”捕
组图:济南放生两千斤鲤鱼遭“疯狂”捕 安徽网库讯:皖能铜陵公司青年突击队抗
安徽网库讯:皖能铜陵公司青年突击队抗 安徽网库讯:何树山副省长到皖能马鞍山
安徽网库讯:何树山副省长到皖能马鞍山 黄山秋色醉游人
黄山秋色醉游人 威马汽车陷退订风波 产品退订率高达三成
威马汽车陷退订风波 产品退订率高达三成 庐江县郭河镇:教育扶贫政策宣讲温暖了
庐江县郭河镇:教育扶贫政策宣讲温暖了 庐江县郭河镇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
庐江县郭河镇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